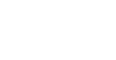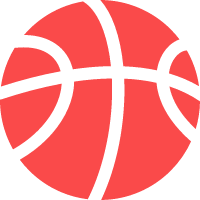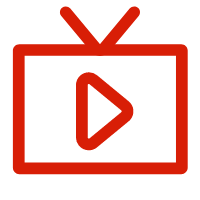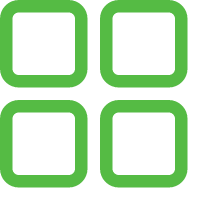里帕特

奔跑在里帕特的黄昏
体育场巨大的阴影斜斜铺开,吞没了东看台最后一排座椅。我系紧鞋带,听见远处传来模糊的哨音——那是少年足球队在加练。空气里有汗水的咸味和草皮被晒过的焦香。就在这个平凡的黄昏,我突然想起了里帕特。
不是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编纂图像学手册的切萨雷·里帕,而是我少年时的田径教练。我们都叫他“里帕特”,带着一种亲昵的戏谑。他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运动服,小腹微隆,却有着羚羊般细长的眼腱。他说话不多,但每个字都像钉在跑道上的起跑钉。“摆臂不是摇橹,”他会突然按住我过度用力的肩膀,“是钟摆。让重力帮你。”
此刻,我沿着空荡荡的跑道慢跑。第四道,他当年指定的“思考的道次”。他说最内道太逼仄,最外道太孤独,第四道刚刚好,既能看清全局又不失自己的节奏。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,我数着自己的呼吸,忽然在某个换气的间隙,理解了那种“刚刚好”的哲学——它不仅是跑步的节奏,或许也是与生活和解的姿势。
第二圈经过弯道时,我又想起里帕特的另一个画面:雨后初晴的傍晚,他指着积水倒映的天空说,“看,云在下面跑呢。”那时不懂,现在忽然明白,他是在说视角——当你倒过来看世界,重力和方向都有了新的可能。就像跑步,看似是向前的线性运动,但真正的超越,往往发生在你与自己的重力达成默契的瞬间。
最后一圈。我加快了些速度,不是为了冲刺,而是想抓住正在消逝的光线。风穿过看台的缝隙,发出空阔的鸣响。里帕特退休多年了,但他的声音好像还留在这塑胶颗粒里,留在这每日不变的黄昏仪式中。体育最深的馈赠或许就在于此:它通过最身体的记忆,教会我们最抽象的道理——关于平衡,关于视角,关于在固定的轨道上如何保持内心的自由。
冲过想象中的终点线时,我并没有停下。跑道还在延伸,而里帕特的第四道哲学,已经内化为一种生活的步频,不疾不徐,向着下一个黄昏,匀速前进。